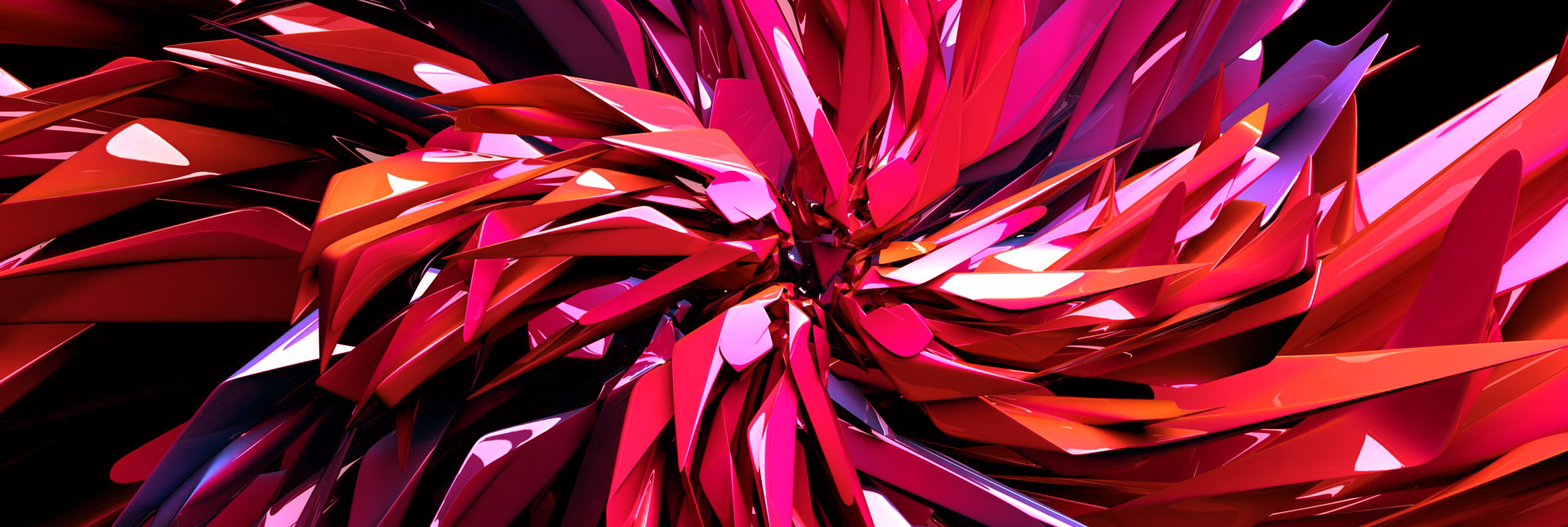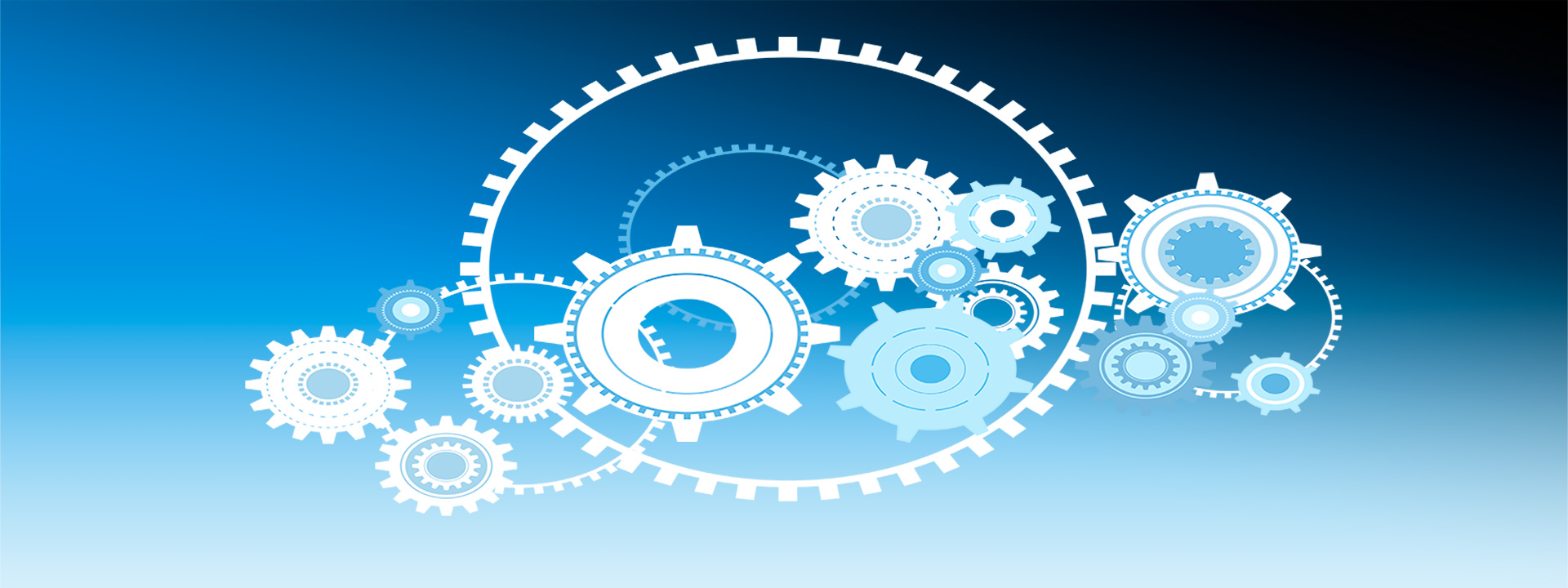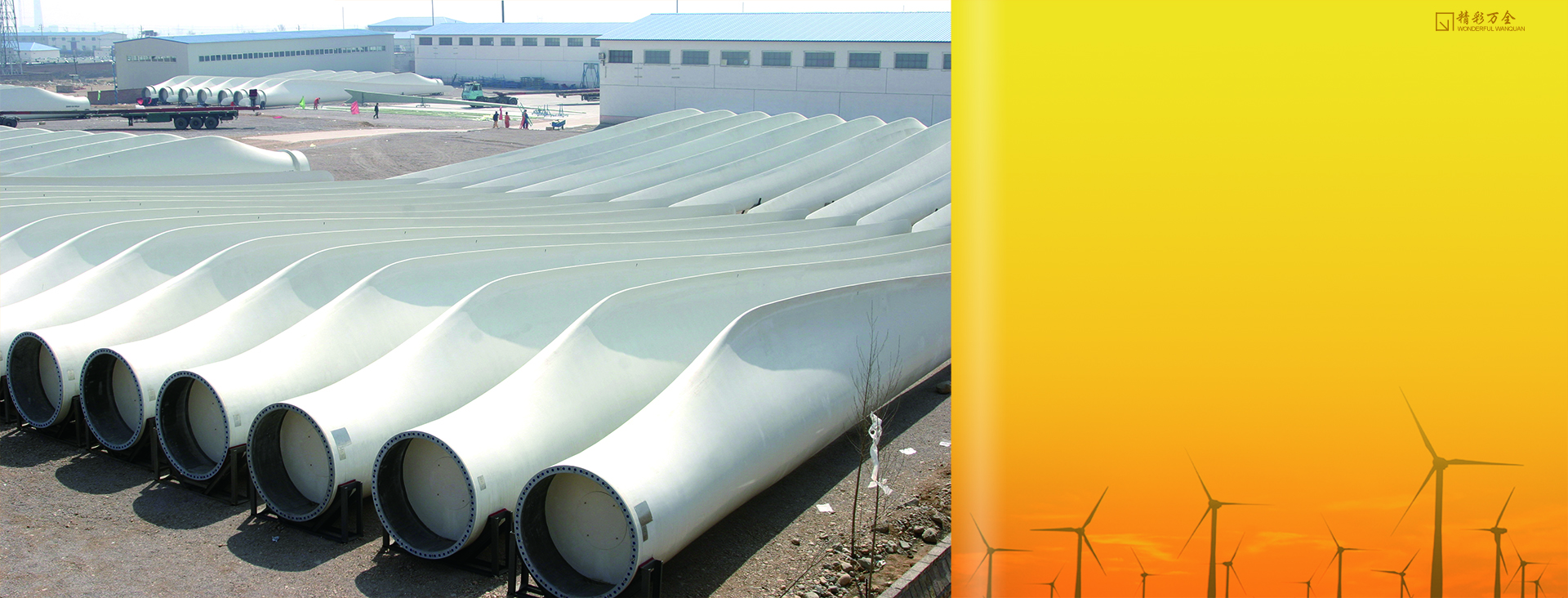产品展示
当前位置: > 凯发在线入口 >
新媒体创作自由的艺术规约(二)
- 产品名称:新媒体创作自由的艺术规约(二)
- 产品简介:画面缺乏重点画面人物画面锐度画面却十分耐看画面锐度不够画面色彩和谐度画面色彩铝型材凯发在线入口画面仍显单调新媒体文艺的创作自由,不只关乎媒介变迁的技术认知,更蕴含着人文审美的艺术哲学。无远弗届的艺术传播自由、拉欣赏的艺术选择自由,以及间性
产品介绍:
画面缺乏重点画面人物画面锐度画面却十分耐看画面锐度不够画面色彩和谐度画面色彩铝型材凯发在线入口画面仍显单调新媒体文艺的创作自由,不只关乎媒介变迁的技术认知,更蕴含着人文审美的艺术哲学。无远弗届的艺术传播自由、“拉欣赏”的艺术选择自由,以及“间性主体”的艺术交往自由,让赛博空间的文艺创作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但创作主体文艺创造力的限度、新型媒介的表达限度和文化资本之于艺术适恰性的商业限度,又让新媒体创作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并且,新媒体文艺的跨界与规制,创作者的自律与他律等,均彰显出创作自由与艺术规约之间的逻辑统一性与艺术必然性。
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提出,电子媒介长于“拟仿”(simulacrum),产生的是“仿像”(simulacra),使用这种媒介犹如“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凯发在线入口,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因为“其中的符码、语言和交流的意义暧昧不清,而现实与虚构、外与内、真与伪则在这种暧昧意义的波光中摇摆不定”。这样的描述虽不免有些夸张,但相较于传统媒介的艺术生产,电子媒介如新媒体创作的规约更少、自由更多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创作的跨界就是它的必然结果;而跨界与规制的并存与博弈所打造的新媒体文艺的生态格局,正是创作自由与艺术规约观念相伴相生的现实呈现。
首先是从文学跨界到艺术。这里所说的文学跨界到艺术不是说的网络作为“宏媒体”和“元媒体”可以兼容各种艺术门类,如可以在网络上看电影、看电视、玩游戏、听音乐等,而是指让文学创作本身跨界到艺术领域,使作品成为文学与艺术兼容的“综合体”。我们知道,与书写印刷文学的文字媒介相比,网络文学创作可以便捷地使用多媒介和超文本技术制作视频、音频与文字相融合的作品,这种作品既具备文学的特点(可以阅读),又拥有艺术的功能(可以有音乐、音响,也可以配图片、图像、影视剪辑等),实际上是一种数字化的综合艺术,这正是我们在《网络文学概论》中界定的狭义的网络文学,也是足以区别于传统纸介文学的真正的网络文学。这样的跨界创作在欧美国家的超文本文学中较为常见,如迈克尔·乔伊斯的《下午,一个故事》(1987)和《暮光交响曲》(1997),史都尔·摩斯洛坡的《胜利花园》(1993)、谢莉·杰克逊的《拼缀女郎》(1995)等,考斯基马将其称之为动态文本(kinetic texts)、生成性文本(generated texts)、运用代理技术的文本(texts employing agent technologies),或统称为赛博格文本(cyborg texts),并提醒我们关注“当前数字化世界中‘我们的所做和所看’与‘我们思维中的惯性’之间的差异”。汉语网文作品的这种差异,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的文学网站如“妙缪庙”“涩柿子世界”中有过生动体现,产生过一批带有“综合艺术”特点的超文本作品,如《超情书》(代橘)、《蜘蛛战场》(苏绍连)、《诗人行动》(米罗·卡索)等。我国内地早期的文学网站上也曾出现过诸如《晃动的生活》(亿唐网)、《阴阳发》(网易社区)这样的多媒介小说。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作品当属《哈哈,大学》,这部反映大学校园生活的网络小说,其文字部分由上海某大学大四学生李臻完成,多媒体部分由他的同学组成的“哈哈工作组”制作。由于文字表达的故事情节需要配有视频、音频的内容,因而作品只能在网络环境中欣赏。后来,2003年漓江出版社将其出版成为纸质书时,只能下载文字部分,音频被舍弃后,其视频部分则挑选了若干幅典型的画面以截图方式穿插于书中。该书的序说:“对于《哈哈,大学》而言,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本革命’——中国首部多媒体小说。读者既可以在纸媒上阅读,因其多媒体小说的文字独立成章,独立叙事;又可在电脑上阅读,用这种方式时,读者既能看到文字,同时又观看了多媒体影像。”类似这样的多媒体小说,是文学,也是艺术,是网络文学向艺术跨界的一次成功实践。
然后是从艺术跨界到文化。正如“文学艺术”本身就是“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新媒体艺术也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新媒体艺术还能直接生产网络文化产品,即不是在宏观归类的意义上,而是在产品品质的分辨上它就是“文化产品”,或者主要是“文化产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作品”。譬如,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设计、网络二次元制作等等,可以说它们是新媒体时代的新型艺术,但其实将它们归于大众文化产品可能更为合适,因为不仅其娱乐性大于艺术性,而且它们的文化消费性也多于艺术审美性,新媒体文化的天空主要就是由它们来支撑的。再如文学作为传统的“语言艺术”,既是“艺术之母”,也是“文化之根”,但是,在网络文学创作中并不是只有“作家”才去当“写手”的,“人人都能当作家”的网络平权机制,让这里成为表达和倾泻的广场,那些“准文学”甚至“非文学”的产品常常与文学作品并陈于网络空间,加上近年来传统文艺学领域出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跨界和扩容趋势,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丰富实践,使得“文学”与“文化”不断交织渗透、界限模糊,让“僭越文学”的网络跨界写作有了更多理论与实践的合法性。于是,在网络文学中,生活与艺术、纪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模糊,常常是混搭在一起的,用“网络文化”的“大箩筐”倒是正适合容纳它们。其实,汉语网络文学在诞生之初,本不是基于文学的动机,如它产生的源头——1992年诞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以alt.chinese.text为域名的互联网新闻组(简称ACT),就不是专为文学成立的,而只是一个华人留学生用母语表达异国游子思乡情怀的文化平台。此后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中文电子刊物,如加拿大的《红河谷》,德国的《真言》,英国的《利兹通讯》等,也主要发表纪实性的文章,发布文学作品的《橄榄树》《花招》等专门文学网站的出现是在这之后的事。中国本土第一家大型原创文学网站“榕树下”,早期发表的作品中,纪实性的文章就占50%以上,其中,心情告白、网恋故事、琐屑人生、旅游笔记、校园写真等占比最高。文学网站专以“文学”为承载和经营目标是在类型小说大范围出现以后,即使这样,今日网络文学平台上在作品也不是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四分法”可以囊括得了的,那些二次元的作品分明就是“Z世代”文化、青年亚文化的数字化表征,那些为网游、网络大电影、动漫而创作的故事桥段,以及粉丝互动中的长短评表白、自媒体中的精彩段子,也是文学与文化交织、文学向文化跨界的产物。
还有艺术类型、文本文体的跨界。可以说凯发在线入口,新媒体文艺的所有形态都是艺术与技术“杂交”的产物,是“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跨界融合。比如,网络音乐、网络绘画、网络设计(艺术设计、产品设计),虽然吸纳了传统艺术的规律与技法,却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音乐、绘画以及美术(平面)和雕塑(立体)设计,用艺术化的技术方式让它们成为独立的艺术新品类。网络大电影、网剧与传统的院线电影、台播电视剧的区别,显然不限于制作成本、播放平台和分账方式的不同,更有创作理念、技术手段、作品容量和消费对象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它们正“自立门户”,试图从传统的影视模式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网络艺术形式。还有市场号召力更大的网络游戏、网络动画则完全成为跨界融合的艺术新类,它们不仅有精彩的故事脚本,更追求能吸引消费者视听感官的技术制作,并添加了传统艺术所没有的其他元素——如网游要有玩家(消费者)的互动参与才能在“过程”中生成作品;不仅如此,无论是互联网游戏、单机游戏还是手游,都必须有游戏运营商提供服务器或游戏客户端下载相关软件,再经由用户的数码处理终端作为信息交互窗口,作品才能在“玩”的过程中“创作”出来,其创作主体完全是“间性”的、多元的、无限衍生的。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游戏的技术操控远远大于它的艺术含量,其文化产业价值也多于艺术审美价值,它所达成的娱乐、休闲、交流和博取虚拟成就的功能,是超越任何一种单一艺术类型的,以至于“网游成瘾”成为一种青少年亚文化滋生的“现代病”。网络文学的文体跨界更是为新媒体创作的文体变迁吹响了“集结号”。我们看到,基于网络创作的“文学”打破了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文体类型,为新文类的产生创造了新的可能。例如,自2003年起点网创立“付费阅读”模式以来,由“续更”与“追更”相伴而生的类型小说,已发展出近百个大类和数百个亚类,玄幻、仙侠、盗墓、穿越、宫斗、悬疑……目不暇接,创造了中外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文类奇观,而不同文体之间的跨界更是网络写作常见的“任性”之举。譬如,在传统的文体观念中,诗歌文体的基本形制是分行排列,而小说是文字的线性延伸,一般不分行排列,但互联网上的第一部长篇言情小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通篇却是分行排列的短句,如:
如果一部小说的通篇都使用这种分行排列却并不押韵的表达方式,那么它究竟是小说还是诗歌呢?痞子蔡就为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全是由短句分行排列的“网恋”小说,吸引了无数粉丝,它对诗歌文体的跨界并无违和之感。另有一部网络小说《玫瑰在风中颤抖》,在文体上也不类前人,因为它不是由作者风中玫瑰独立完成,而是在BBS公告板上由作者和众多读者现场回帖、参与互动、一段一段贴出而共同完成的。该作品共约14万字,断断续续历时9个多月完成,其中属于作者写作的部分仅有三分之一,其余均是由众多网友互动跟帖完成,内容上则相互衔接,合力推动着一个“婚外恋”故事的进展。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风中玫瑰》的书名出版了这部BBS小说,这样的混搭型文体恐怕只有网络媒介创作才会出现,也才有可能。另外还有如千夫长的手机短信小说《城外》,“段子写手”戴鹏飞的原创短信专辑《你还不信》,被称作“中国首部微博小说”闻华舰的《围脖时期的爱情》,以及微信APP诞生后,在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中涌现的微信文学等等,它们在文体上已不限于诗歌、小说、散文,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不再是那么了了分明,数字化新媒介创作让新的文学文体不断展露在网络的虚拟空间。
由于技术、艺术、资本、市场、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合力作用,特别是“IP”观念之成为行业风标后,我国的新媒体文艺市场经历了“文学→艺术→文化→娱乐→产业”的层层洗礼,“跨界”不仅成为常态,也是它的存续之道。不过,在此我们依然要说,新媒体创作无论多么自由、怎样跨界,都是艺术规制下的自由、媒介限度下的跨界,是“戴着镣铐跳舞”、循着目标远航。作为一种人文性精神文化生产,新媒体创作的规制仍将以其逻辑的必然性彰显出艺术的合理性。
首先是艺术审美规制。艺术审美是文艺的底色和创作的“靶的”,新媒体创作也不例外。比如,网络作家中可能不乏“文青”和才子,如早期写手安妮宝贝、李寻欢、邢育森、黑可可,后来写出了《网络英雄传》系列的刘波、郭羽,创作《将夜》《择天记》的猫腻,创作《赘婿》的愤怒的香蕉,以及骁骑校(《匹夫的逆袭》)、陈词懒调(《回到过去变成猫》)、冰临神下(《孺子帝》)、何常在(《浩荡》)等人凯发在线入口,他们的作品文学味比较浓,创作的多为值得“细读”的耐看之作。但毋庸讳言,网文圈中的多数写手并非是冲着“文学”而走进新媒体,走进网络写作的,怀着功利化商业动机、娱乐性消遣目的者上网“试水”者甚多,加之网络写作的“后置型”生产模式,重“出口”不重“入口”,准入门槛不高,缺少严格的把关人,导致网络文学中赝品和平庸之作较多,这也正是网络文学饱受诟病,有的格调不高,乃至需要“净网行动”“剑网行动”不断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网络并非文外飞地,网络文学既然是“文学”,就仍然摆不脱文学的要求,不能没有艺术审美的规制。网络作家何常在说过:“从纯文学到通俗文学性再到网络文学,并没有感觉到有多大的区别,本质上来讲都是文学,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众艺术。”也就是说,网络文学作品无论是谁在写、不管是写什么,都需要按照艺术审美的要求,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创造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网络”不是理由,“业余”也不是借口,“文学性”的艺术魅力才是网络创作绕不过去的“铁门坎”,如果“创作自由”是它的理想,“审美规制”就是它的宿命。
其二是道德伦理的规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在论及网络文学评价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网络文学应该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基本的法理和道德底线。在反映现实时,应当分清主流与支流、光明与黑暗、现象与本质、现实与理想、合理性与可能性,恪守基本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不能否定一切,怀疑一切,“天下乌鸦一般黑”,“洪洞县里无好人”。哪怕是虚构玄幻世界,也应当符合人类既有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常理,体现人性人情。
网络写作的轻松和随意,以及娱乐至上和过度商业化的传媒语境,可能淡化创作者应有的责任,造成网络写作崇高感的缺失,文学与“时代良知”“人民代言”的价值理念越来越远。其结果,网络技术传媒与大众文化合谋,其生产的产品传递的往往不再是昂扬向上、刚健有为的价值观,也不再注重高尚情操、英雄情怀的讴歌与酿造,而可能只是自娱自乐的一己表达、迎合市场的文化快餐甚或成为公共空间的文化噪音。故而,网络创作不能没有道德伦理的规制,应当倡导高雅的审美取向,追求积极、健康、乐观、高雅、清新的审美趣味,反对消极、颓靡、悲观、低俗、污浊的审美趣味。互联网并不只是冷冰冰的机器,作家面对它实即面对生命、面对人生、面对鲜活的生活,因而应该对文学心怀敬畏,对网络志存高远,并把这样的观念体现在自己的题材选择、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语言使用、文本格调等创作过程的始终。
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制。如果你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价值赋予、一种观念构建,或一种精神的表达,就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营造和体现。传统文艺创作是这样,新媒体创作也不例外。无论新媒体文艺多么另类甚或叛逆,不管其媒介载体、创作技能、传播途径和欣赏方式与传统文艺有多么不同,只要它还是文学艺术,只要它还属于精神产品,它就应该具有作为精神产品所必具的基本特点,都需要蕴含特定的意义指向和文化价值观,并应该让它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力与感染力,使其成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青少年成长的精神“钙质”。我国的新媒体文艺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有两大举措,一是监管,二是引导。前者通过相关政策法规、行业自律、文艺创作者培训等,净化网络空间,打击和清理不良作品,从而设立意识形态方面的底线和红线;后者则通过评优设榜,设置网文标杆,积极引导新媒体创作承担时代使命,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创作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培根铸魂。例如从2015年起,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作协每年都推出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榜单,其意义旨在传播正能量,讴歌真善美,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如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推出的25部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中,《大江东去》力呈改革开放40年的波澜画卷,《大国重工》勾勒国企发展的任重道远,《太行血》尽显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家国情怀,《繁花》展现平凡人不平凡的生活百态,《地球纪元》书写绝境下人性的抉择和坚守,《魔力工业时代》将科技原理与丰富想象融会贯通……其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就具有积极的意识形态内涵,以此赋予网络文学创作以坚实的逻辑支点和底气,蕴含着网络写作的意识形态向度。
新媒体时代的主体自律与他律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我们不妨从一部作品说起。网络小说《网络英雄传之黑客诀》发布后,引起了许多读者对网络安全、信息风险问题的关注。作品描写的黑客高手在反恐禁毒领域的巅峰对决,不仅在艺术感受上让人惊心动魄、在技术上使人脑洞大开,也让我们深深感触到互联网时代尖端技术的无所不能和信息风险的无处不在,在黑客高手面前似乎一切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私可言,大到国家的通信卫星、军事指挥系统,小到马路交通信号,个人手机、银行账号、私人通信,凡是有电源、有网络的地方,都存在安全风险。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却揭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计算机网络的便捷,在给予人们充分自由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限制——新型媒体尤其需要培植“鼠标下的德性”,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管控让一切与网络有关的信息变得“透明”,任何一个主体的网络行为都将无处遁形,也都将影响社会公共空间。于是,如何处理新媒体语境中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主体行为的自由度与虚拟社会的行为规范的关系,以及网络行为与道德意识的关系等,便成为数字媒介伦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新媒体文艺而言,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需要重新构建自律的约束机制与他律的行为规范,以调适创作自由的艺术规约,构建创作自由与艺术规约之间的逻辑统一性与艺术必然性。
其一,“角色面具”消解后的身份自律。网上有名言说:“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只是就网络的匿名性特点而言的,千万不要据此以为,上网时没人知道你是谁,就可以在虚拟空间肆意妄为。事实上,由于网络IP地址的唯一性和现代社会广泛覆盖的视频监控,如果需要,不仅知道上网者是哪条“狗”,还可以清楚地知道你上网做了什么,并要求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匿名上网是有“角色面具”的,网民可以化身为任何一个他想要的角色与他人交流,此时,网民暂时摆脱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和“身份焦虑”,他不再是社会关系、环境伦理约定的某一社会角色(职位、身份等“社会关系的总和”)或家庭角色(家长、子女等血亲人伦关系),而是一个平等交流的普通网民。这时候,他是自由的、轻松的,但此时的你决不能放纵自己的言行,而需要“慎独”和自律,因为你所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虚拟的广场,而是公共话语平台。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文字(或图片、音频、视频)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对社会负责,文艺表达的东西还得对文艺接受对象和文艺本身的创作与发展负责。可见,这个貌似“孤独的狂欢”的私密环境,其实是一个交互式共享空间,即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互动式社会”。于是,当一个人的现实角色被匿名上网暂时(只是暂时,不是永远)消解后,一个有责任感的理性网民,需要的是“不忘初心”,用自律坚守道德、信念和法规,在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交往自由与社会责任、平等与互惠之间,把握好必要的平衡和一定的度,而不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网络空间滋生的谣言、诈骗、窥探隐私、黑客犯罪,某些网络作品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恶俗、低俗、庸俗或、暴力、迷信等有害内容,正是面具隐匿后丧失身份自律的表现。
其次是虚拟沉浸中的理性自律。被称作“赛博空间”的互联网是一个足以让人沉浸其中乐而忘忧的世界,一个既非物质亦非精神、却又关涉物质与精神的“数字化世界”。随着VR (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MR(Map Reduce混合现实)和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抑或佩戴数字引擎、头盔显示器、数据服、数据手套等虚拟工具以后,互联网将以更为强大的沉浸性虚拟而大大增强更为“真实”的虚拟式沉浸,让网络游戏、网络影视、数字动漫等新型艺术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宠,把虚拟沉浸中的理性自律,从技术和艺术层面,提升至技术哲学和文艺社会学论题,并成为网络文艺美学的一个支脉。就新媒体文艺来说,作为媒介载体的网络世界不仅作为一种“此在”是虚拟的,艺术所表现的对象也是“超现实”的、想象的世界。笔者多年前曾描述过这个世界:“网络作品所描写的是网络化了的生活世界,甚至是独立于现实又迥异于现实的虚拟真实世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衍生为写作与超现实的虚拟关系,不仅艺术与现实间的‘真实’关联失去本体的可体认性,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联也被‘赛博空间’所隔断。于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就变成了人与网络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创作成了一种‘临界书写’,作品显露的是一种客观本体论与价值本体论双重悬置的‘镜映效果’。”作者在虚拟的世界里沉浸,读者特别是那些等待续更的“忠粉”“铁粉”们也将被“代入”到这个世界不能自拔,感性覆盖理性、情绪激发情感、“爽感”遮蔽知性,会成为新媒体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常态。此时,理性的干预、意志的自律不仅是必要和重要的,也是必然和应然的,因为正如尼尔·波兹曼用“娱乐至死”的警言所揭示的:“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再者是话语自由情境下的艺术自律。新媒体催生文艺话语权的下移,让“零门槛”的创作自由和表达自主情境下的艺术自律问题浮出水面。并且,新媒体创作“”式的爆发式增长,使创作规范和艺术约束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成为一个需要仔细考量和重新设定的艺术规制。否则,有“网络”而无“艺术”,或有“文学”而无“文学性”将成为新媒体文艺良性发展的一大“软肋”。这种艺术自律的必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的艺术素养提升,二是新媒体生态语境中的艺术坚守与自觉。前者需要网络创作者以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担当,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水平,怀着对艺术的敬畏、对创作的虔诚去从事新媒体文艺生产,从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艺术经典中汲取营养,向古人学习,向他人学习,把对人文审美艺术的追求变成无限追求,让追求本身成为无限。后者则需要摆脱消费社会的功利诱惑和来自“追文族”“艺术忠粉”“打赏一族”的互动干扰,不要为一时的“利”与“名”而迷失自我、走偏方向。譬如,一部网络小说的连载与更新会伴随着无数粉丝的关注、兴奋、议论,抑或粉丝之间的交流、争论乃至互怼、掐架,从而形成读写互动中草根群体与作者之间的“绑架关系”,形成“共同体意识”,其带来的结果可能让“作者的生命表达与独异创造难以为继,独立的写作意志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对大众意淫思维的遵行”。此时的作者能否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初衷,对他的艺术自律品格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另外,出于商业目的,一个作品能否在网站获得首页推荐或上架、榜单前推,要依赖网友的点击、收藏、推荐、打赏、月票等各项数据,网络写手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爱好可能降格以求,拉低作品的艺术品位以获取阅读市场的消费业绩,商业利益的巨大诱惑也将是对创作者艺术自律情怀的严峻考验。
再说说创作主体的他律问题。概括来看,这种他律,以文学传统、政策法规、消费市场这三种因素影响最大。其中,文艺传统的他律是对新媒体创作的内因规约,政策法规是对行为主体的外在规制,而消费市场则构成新媒体文艺创作的商业驱动。
传统的规约力量是潜在的,柔性的,也是巨大的,深远的,无所不在的。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艺术传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浸透在新媒体创作、传播、欣赏、交易的各环节中,对文艺的评判、价值、影响力形成影响。例如,人们对网络文学的批评如“乱贴大字报”“口水文”“量大质不优”等等,实际上是基于他们心目中“何为文学”“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好文学”来做出评判的,而评判的标准就是文学传统,或传统的文学认同标准和文学观念。中外文学传统已积淀数千年,人们对文学已有公认的评判尺度和经验。譬如,大凡是文学,不管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该是一种人文性的审美行为,其所表现的都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网络创作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一种特定的意义承载和价值赋予。再如,网络文学只要还属于精神产品,它就应该具有作为精神产品所必具的基本特点,都需要蕴含精神产品特定的品质,都要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引导人们向善、求真、审美,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性情。新媒体改变的只是文学载体、传播方式、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如情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张抗抗)。不同时代的文学或许各有其媒体技术方面的差异,但“体验、想象力和才华”是能少的(王一川),如果少了,它就将不再是文学。《择天记》《巫神纪》《斗破苍穹》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建构出浩大磅礴的神魔或修炼谱系,均可在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梦入神机、辰东、我吃西红柿、血红等网络作家的作品受到众多网友追捧,其实正是传统武侠、玄幻小说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的一种延续,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是传统的“他律”作用于网络作家“自律”的结果。
政策法规的制约力量是直接的、刚性的,并且是强制性的凯发在线入口,其效果也将立竿见影。例如,我国曾出台过一系列与新媒体文化、网络文艺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2010年以来,国家版权局、网信办等部门组织开展的“剑网行动”和“净网行动”,每年都要查处一批网络盗版侵权案件,一些涉黄、涉政、涉黑、涉爆的网络作品被清理,还有一些不合规范的作品由网站平台主动下架,2019年上半年,仅起点中文网贮藏的小说作品就下架超过120万部。法律法规对网络文艺的“他律”举措,对于约束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版权,打击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促进整个行业健康长远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
较之于传统文艺创作,消费市场的他律性约束将更加直接,也更为强大。在高度市场化的新媒体文艺领域,消费者者就是创作者的“衣食父母”,一部作品如果不被消费者接受、欣赏,一个创作者如果缺少粉丝关注,就将消逝在无边的网海。如同传统的文艺市场一样,一个视频产品如网络大电影、网剧、网络动画片,甚至网络综艺,如果没有观众,网友不爱看,没有点击率,少有消费者为视频买单;同样,如果一部网游缺少玩家,一个网络音乐没有听众,不仅创作者、制作方和发布平台在经济利益上会亏本,艺术上也会是落空和失败的。于是,新媒体文化消费市场的约束力将会对新媒体创作形成倒逼作用,迫使新媒体艺术生产一方面提升作品质量,力求思想精神、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以打造精品力作;另一方面,要了解市场需求,适应消费者需要,让消费市场的他律性约束成为创作的驱动力。从新媒体产业链的上游——网络文学创作来看,一个写手要想在网络上立足,必须拿出能让网民读者喜爱的作品,一切都要凭借作品说话,任何人都无法干预读者的选择。新媒体作品的市场化竞争十分残酷却也非常公平,它不会埋没任何一个勤于写作的文学天才,也不会给任何一个庸才以鱼目混珠的机会。一个作品的媒体影响力如百度指数、微博指数、微信指数,一个创作者的社交平台影响力,如微博粉丝量、贴吧热度,以及该创作者与作品的综合影响力,如点击量、购买人数、推荐量、评论量、收藏量、粉丝量、打赏数、月票数、豆瓣评分等等,均是衡量新媒体创作市场号召力的硬指标,它们无时不在推动或制约着创作,形成一种无时不在的他律性驱动机制。正是凭着读者市场的影响力,唐家三少、天蚕土豆、我吃西红柿分获由“橙瓜网”评审的2016、2017、2018年“网文之王”称号,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庆余年》豆瓣评分达7.9分。创作了《遍地狼烟》等现实的网络作家菜刀姓李(李晓敏)曾深有感触地说:“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真正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决定作品命运的人变了:以前是编辑决定作品生死,到了网络上更多地是由读者来判定作品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写手由迎合编辑或者文学期刊变成了直接取悦读者。”网络文学创作是这样,网络艺术创作何尝不是这样?这正是新媒体创作自由与艺术规约之间存在逻辑统一性与艺术必然性的又一注脚。
[22]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20页。
[23] 该书对网络文学的概念做了三重界定:广义的网络文学是指经电子化处理后所有上网了的文学作品,即凡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文学都是网络文学;本义上的网络文学是指发布于互联网上的原创文学,即用电脑创作、在互联网上首发的文学作品;狭义的网络文学是指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制作的作品,或者是借助特定创作软件在电脑上自动生成的作品,这种文学具有网络的依赖性、延伸性和网民互动性等特征,最能体现网络媒介的技术特色,它们永远“活”在网络中,不能下载做媒介转换,一旦离开了网络就不能生存。这样的网络文学与传统印刷文学完全区分开来,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实际上它已经脱离了“文学是语言艺术”的传统观念,而成为一种新型的综合艺术。参见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4] [芬兰]莱恩·考斯基马:《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单小曦、陈厚亮、聂春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页。
[25] 有关多媒体、超文本网络小说信息可参见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第五章:存在形态:电子文本的艺术临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64页。
[26] 李臻、哈哈工作组:《哈哈,大学》,吴纪椿所作的序,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7] 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8] 王志艳、陈杰:《作家何常在:网络文学的说法早晚会消失,只留下文学》,新华网客户端:
[29] 陈崎嵘:《呼吁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人民日报》2013年7月19日。
[30] 郭羽、刘波:《网络英雄传之黑客诀》,咪咕阅读、花城出版社2019年9月网媒、纸媒同时发布,是《网络英雄传》系列小说的第4部。
[31]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页。
[32] 欧阳友权:《用网络打造文学诗意》,《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33]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34] 参见黎杨全:《数字媒介与文学批评的转型》,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8页。
[35] 近年出台的代表性的法规文件有: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00年9月25日);文化部《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1年4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13年3月1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12月18日);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5年10月3日);国家版权局《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2016年11月1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2017年7月1日)等。
[36] 有统计表明,起点中文网此次下架的小说中,玄幻频道少了35万本,奇幻8万本,武侠1.4万本,仙侠14万本,都市21万本,现实1.4万本,军事4万本,历史5万本,游戏7万本,体育7千本,科幻8万本,灵异3万本,女生7万本,二次元7万本。
[37] 王觅《网络文学:传递文学精神,提升网络文化――中国作协举办网络文学作品研讨会》,《文艺报》2012年7月13日。
 凯发在线入口
凯发在线入口